比如說我非常欣賞的一位經濟學家黃亞生,現在在MIT工作,他就解釋中國的鄉鎮企業為什么成功。當時的西方學者,包括一位得諾貝爾經濟學家的學者,他分析中國的鄉鎮企業為什么成功,因為中國的鄉鎮企業代表了一種新型的、超越古典經濟學的一種發展模式,因為鄉鎮企業的產權是屬于鄉鎮政府的,那既然政府所有的企業都能發展的這么好,那就是說不一定要有清晰的產權才能發展起來。這是當時西方非常流行的一種對于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
那黃亞生當時就回到中國,做許多經驗調查,搜集無數的檔案,就發現中國的鄉鎮企業其實90%本質上都是私營企業,只不過為了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開展工作,才不得不名義上掛靠在政府的名下。
我的意思就是,當你發現了這個研究的問題“是什么”之后,那么“為什么”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認為“頭重腳輕”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害的,這也是我希望傳達給你們的一些經驗教訓,希望你們不要被大的理論、經驗所嚇倒,仔細地老老實實地把到底在發生什么這件事情搞清楚,無論是當代中國在發生什么,還是歷史上發生了什么,把這些東西搞清楚,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后來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從經典到經驗》,引起了很多爭論。很多人批判我說你怎么教導小孩子不要讀經典,其實并不是。我是認為讀經典很重要,但是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是更重要的。應該是從經驗里面提煉出來的,而不是說相反的方向。
現在我開始講最后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其實可以從我之前講得東西中引申出來。最后一個階段就是所謂的“從頭到來”這個階段,我是以30歲的高齡才進入到這個階段的,我覺著是要從真問題出發,你關注什么你就去讀什么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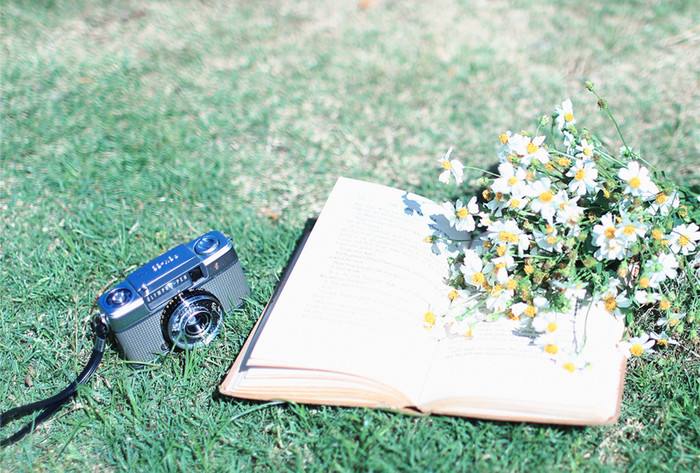
比如說我在27歲左右開始在網上讀一些東西,我會發現許多有震動性的東西,當時我讀到許多關于中國大饑荒的問題,在當時對我來說是非常震撼的。當時我關心的問題就是中國革命到底發生了什么,這是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問題,所以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寫有關中國革命的。包括后來我關注“民主”這個東西到底適不適合中國,包括寫《民主的細節》,也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真誠關心什么問題,我就會從這個問題出發去思考,去讀書。我覺著這樣去讀書,真的會很有收獲,也會非常有樂趣。它不在是一種人云亦云的狀態,而是小孩子在大自然里發現一種草叫什么、一種星星叫什么的歡愉。
從真問題出發也需要大家有發現問題的能力,你要看到一個現象之后努力去發掘現象背后有什么理論問題。
比如說以前,當我看到一則新聞時,它就是一則新聞而已,但是現在我會去思考這個新聞背后有什么問題。我現在看到電視里報道菲律賓的腐敗案件,我就會想民主國家也會有這么多的腐敗,這就是你穿透一個新聞去看背后的問題的方法。你看最近利比亞的局勢,你就會去想為什么同樣是中東國家,埃及的轉型比利比亞就容易得多,那你就要根據這個問題去找許多書來讀。再比如你看到泰國“紅衫軍”的新聞,你就會想是不是在民主國家民主會導致過度的民主動員。
我的意思是凡是你看到新聞,甚至是看到雞蛋價格變化的時候都會想這個背后會不會有什么理論問題,所以擁有一雙發現問題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讀書思考還有一個問題很重要,是要從實證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理論概念的東西非常重要,因為發現問題的能力主要看你有沒有理論的背景。但是許多問題不可能從推理的方式去回答的,必須從經驗來回答。比如說,舉個例子,美國的民主是不是虛偽?這個你讀再多的馬克思都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他不會有一個現成的答案去告訴你。那你應該去讀什么呢?如果你認為民主的標準是國家出臺的政策應與民眾的利益吻合,那么你就應該去讀這個國家出臺的政策,以及民意測驗的對比,這也是一種方法。你不可能從那些經典著作里找到現成的答案,所以我就鼓勵這種實證的方法。而且我覺著這種實證的方法本質上是一種特別謙虛的研究方法,因為現實總是流變的,實證的方法導致你研究的結果必然是開放的,我覺著這是實證研究非常優美的地方,因為它永遠對所有的答案表現出一種開放的態度。
期待更新